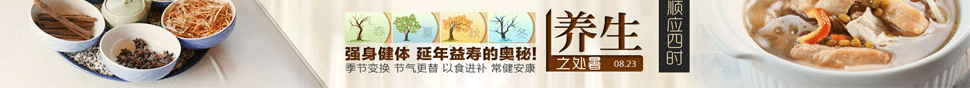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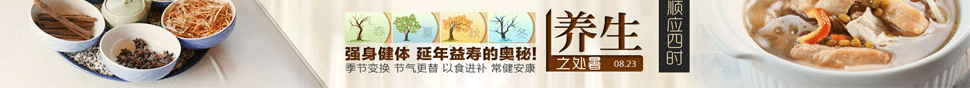
那些草药,一直在身边
(一)
每天,唧唧叫个不停的手机里不断传来与疫情有关的信息,其中一类是各地中医研究出的供预防和治疗用的方药、汤剂,有广州的“肺炎1号方”,又称“透解祛瘟颗粒”;陕西的“中研益肺解毒汤”“中研清瘟护肺汤”;疫区中心湖北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一、二号方……湖南的国医大师刘祖贻等专家讨论制定了2个中药预防处方;祖国的心脏北京发布了分别针对不同人群的4个方子……这些方子的构成以文字、图说、视屏等形式发布出来,我看着、听着。多么熟悉啊,那些草药——芦根、白茅根、金银花、菊花、桑叶、石菖蒲、桔梗花、大青叶、竹叶、苏叶、茵陈、石斛……我认得它们,它们曾在我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里。每走一步,它们中的一枝、一朵、一蓬、一束不经意间会拂过我的脚背,或牵扯一下我那时挂着补丁的粗布衣衫。每走一个季节,它们会在属于它们各自的季节中让我看见并任意采摘。我甚至知道它们中的有些个喜欢躲在哪里。
我想要回去,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庄,一一指认。
比如芦根,这个季节,在那条从村南蜿蜒到村北、宽度为一个少年奔跑着可以成功跃过的港渠边,散在的一丛丛还枯黄着,新枝尚未长出。门口塘西头淤泥里的一大丛也是如此。等到八月,它们长成一年中壮实成熟的模样,父亲收了工,就会腋窝里夹着带回一小捆,湿漉漉的竹节样的白根。母亲仔细掐去茎节上的细毛芽,而后洗净、切段、晒干,拿袋子装了挂到墙上。遇家里有人火上了头,咽喉肿痛,抓一小莋煮水,喝一两碗就有好转。夏天酷热的时候,劳作的妇女们容易得“发热淋”,把这芦根和嗮干的鱼腥草泡了喝,见效很快。而鱼腥草就长在邻居家的屋檐沟边、门前田畈的角角落落。这种草见风就长,到了初夏,一株株牵连着,头顶白花,花心再立一个长长的穗状花冠,在田野中、屋檐下摇曳。一年长过,土里留下了根,年年还要再长,从不爽约。
白茅根更寻常,路旁、山坡、荒草地上到处都是。我小时候不知道它是药,只知道它能吃。放牛的时候,牛吃,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扯来吃。乡村对事物的称谓总是直截了当,白茅根我们叫茅根,就是茅草的根。拔的时候,缓缓地往外提,藏在土里横着长的一节节白根很容易就出来了,到路边沟渠的净水里洗洗,或者一时找不见水,在衣襟上擦两把就嚼起来,清甜清甜的,满嘴生津。
在野外,我们总能找到吃的,像野桑葚、野扁担籽、野李子这样的浆果不算,只说一些植物的根呀茎的。清明时节,野刺贡的芽长得好,择粗壮的吃,甜中带一点微微的苦;夏天,野葡萄藤的嫩尖儿,吃起来酸不溜秋的,解渴得很;还有一种薹样植物(想不起名字了)长在春天,薹杆剥了皮吃,也是酸的,甚至比野葡萄藤尖儿还要酸,特爽口。多年后上了护校,书中得知野葡萄藤也是一味草药,有清热、止血的功效,能治疗麻疹、痢疾、疮疡……心中并不觉惊异。草药、草药,乡村的野草,有多少既是草,也是药啊。三月三,麦田边走过,地儿菜在地沟里开花了,细小的百花举在头顶,这时的它们长到正好、长到季节了,扯一大把回去,烧锅、煮水,煮鸡蛋——难得的几个鸡蛋呢,母亲说,都吃吧,一人吃一个,一年不头昏。小蒜更是四处长得肥实,它们喜欢一小撮一小撮地长,像是专等着家家户户走出去,走到春天里,走到春天的田畴地畈,劳作一阵,出一身微微汗,而后,它们好作为奖赏,被收工的人们顺带着掐几把回去做小蒜粑吃。奶奶双目失明,坐在她的房里一早就闻到了香味:在做小蒜粑啊。她一口牙掉了不少,吃起来嘴扁扁的,唇四周每一条交织的皱纹仿佛都在用力。一边慢慢吃一边说个不停:一开春就欠小蒜粑、蒿子粑吃,春头上热毒多,吃了发发汗、解解毒、去去身上的寒气,不得病……她说的蒿子全在野外长着呢,有艾蒿、臭蒿、茵陈蒿……那种做粑的蒿子,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儿,杆和茎紫红色,叶子背面是白的,阴历春二三月,它们四处冒出来,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带着露水。掐嫩尖儿回来用滚烫的开水泡过,沥干水、切成碎末,或捣成泥,连汁带碎叶和上糯米粘米粉,做成素的蒿子粑,蒸熟了,一片新鲜的绿,一嘴清新的香。这种粑儿到了现在我们家还在做着吃。女儿爱美,买了食物印泥,各样图案的小章子一盖,一锅蒿子粑俨然成为了艺术品。
蒿子,在过去的年月,在我们这由南到北、从东到西,方圆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哪一个乡村的家庭绕得开这株小小的植物呢?母亲给我讲过一个臭蒿子的故事:上世纪的五八年,闹饥荒,家里米缸、菜坛都见了底,饿不过,去野外找野菜,哪还有哦,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天天都在野外找呢。她怀着身孕饿得走不远,村里一个叫“细脚子”的女人因为双脚是被包过的“三寸金莲”也走不远,俩人在附近的一个茅厕边上看到一大片油绿的臭蒿,捋了些回去,和一点米糠煮着吃了。当天没事,俩人高兴死,不敢声张,第二天又悄悄去捋,就这样吃了一些天,不仅熬过了饥荒,还护得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二月里来哟万木发哎,清水无粮灶火塌,田里扒得菜一篓哎,万般世事都放下。”这是深处中原陕西的诗人陈年喜不能忘怀的他的父亲唱过的歌谣。他回忆起父亲唱这首歌谣时,“其音绵长,婉转抑扬,极是凄美,苦涩里有一种生的不舍与不甘”。他说,“这唱词里的‘一篓菜’,就是茵陈”,是他在某一年得黄疸病,他的父亲每天去地里拔回来,一天三大碗煮水给他喝的茵陈草,也是他贫苦的乡亲在饥荒年月挖回家当口粮救命的茵陈草。我少年时有过和他一样的经历:考上中专,第一次出远门去城里读护校,没多久就病了:黄疸肝炎。城市避我三舍,怕我传染,而我的村庄踮着脚迎我,张开双臂抱我。父母支起简易小灶,坐上一只黑黑的陶罐,倒进同样枯黑的草药、凉凉的井水。火苗深情舔着罐底,不一会,罐里就沸了。茵陈草淘气,老要浮在液面上,拿一双竹篾的筷子压了又压。一大碗褐色的汤药,有苦有涩有甜有酸,还有掩不住的茵陈香。我就那样一天天褪去了巩膜的黄、皮肤的黄、血液骨头里的黄,好了。
(二)
——猛火文火中煎熬,陶罐瓦罐里翻沸,一缕药香轻而又轻、浓而又浓,飘拂经年,护佑过诗人,护佑过我,也一定护佑过你。
——神农的百草,种子谦卑,一直在我们脚下的大地。
我的村庄,养出我一双大脚,出门疯跑,脚趾头踢破了,血流不止。疼得刚想哭两句,一看,脚边上有一棵止血草,贴着土长着,椭圆的、密匝匝的细叶上挂满露珠。赶忙扯了些,使劲搓烂了,硬是搓出深绿色的汁来,一把敷上去,摁紧,血一会就止住了。
我的村庄,夏枯草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它们抱团长在挨着水井的那个大田边,一些荒草老是比它们长得高,这样,它们刚好躲起来。我晓得的,早插的谷子黄熟的时候,它们就长老了,变成药了。哈哈,这纯阳之草,和阳养阴之药,我要悄悄去采来,晒干了拿去卖,换我读书的报名费。
我的村庄,桔梗花开得像长角的喇叭,蓝紫紫的在坡地上摇;紫苏长在棉田里,一身深红的“阔”叶像祛风的战袍;马齿苋在一块块红薯地里见缝插针地生着,它们最讨喜,是农人清淡的碗头少不了的佐菜。
我的村庄,有高大的桑树,孩子们春天在树下采桑叶给偎在胸口的蚕宝吃,初夏爬上树摘桑葚自个儿吃,吃得满嘴牙齿发紫。金银花总是随着光阴的游走由白转黄,成双成对,形影不离,妇女们爱把它们别在发辫上、挂在胸前,这时的她们,被太阳晒黑的脸膛,有了别样的美。
我的村庄,到了五月端阳,家家门上插艾草,户户窗前挂菖蒲——“长命缕”,招百福;菖蒲剑,斩邪魔。这天地间的小草,不仅是肉身的药,也是精神的药、意念的药、氤氲一天天平常日子的别有一番滋味的诗意。
九月,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开了。九十岁的母亲,前两年脚力还健着,老蜜蜂一样四处嗡嗡。南边的山脚下采采,北边的菜地里采采。坟山上采采,出村的路边也采采。今天采过,明天晴好还去采。“我看见那些女人哈(都)去摘,我也去摘哦。”她一点不老呢,吃饭有时会颤动的手,摘起野菊花来蛮灵活。不知不觉,她采了一小簸箕。清水里淘洗过,沥干,搁大铁锅上蒸。“那些女人说,锅里要放一花儿盐。”那些女人是村里比她年轻三四十岁的女人们,她们留守在村里带里孙外孙,她们是她的师傅。而她这徒弟灵蔻得很,一点就透。甚至不点也是透的。她说,一花儿盐,刚好添点味,等晒干了好保存。她把蒸过、晒干的野菊花分装到干净的罐头瓶子里,等进了城的儿女们回来拿……她自己留小半瓶,防备嘴里仅存的几颗半截牙齿上火的时候喝一点,满见效。菊花凉,胃不好,她不能常喝。
还有野麻,我又怎么忘得了呢。那一年,我们村里买回了一台崭新的拖拉机。伙伴们都爬上去了,我最后一个提着打猪草的篮子爬上去。感觉还没站稳,就听见“要翻了要翻了”的喊声,惊惶之下,我像个英雄一样跳车了。跳下来摔在地上,右手反折如柳枝。接骨的人说,要一些野麻根,捣烂了,敷在断骨的连接处,再拿柳树皮做甲板绑了,让骨头自己长。我摔断手的季节在晚秋,四野的柴草割得所剩无几,父亲满畈满岭去找野麻,皇天怜悯,他找到了,在一块还没有挖完的红薯地炕边。他三两锄就挖出了麻根,回家来放在洗干净的麻石上捶,小心捶烂了,敷上去。我的手先是感觉凉凉的,而后开始发热,发烫,烫到包裹在柳树皮里的患处皮肤起了大水泡,我一点不晓得疼。就这样,每隔两三天,父亲就会去那里挖一点野麻根回来,交给接骨的师傅给我重新敷一次药。敷药前,师傅口含白酒,噗地一下喷到患处,而后在上面推来赶去,真疼啊,疼得脚直打颤。一溜儿野麻根快挖尽的时候,我的骨头长好了。至今,这只右手活动自如,粗活细活忙忙碌碌几十年,从没有一点妨碍。
——这是怎样的缘分,怎样的恩情!
,大疫之春,大地上的草药依然在我们身边。这神农的百草,曾经趟过了多少灾难、多少险疫!受难的同胞,不要恐慌,有它们在,就有福佑在。且让我们心怀感恩,和草药联合,坚强抵抗。
写到这里,央视传出一个好消息:今年秋季起,小学五年级将陆续开设中医课,先在浙江省试点,然后在全国范围展开。这是让人振奋的好事。该从哪里开始呢?
孩子,疫情结束了,天气暖和了,到野外、到乡村去学中医吧。先认认草药。如果你想一辈子记住一棵止血草,赤脚奔跑吧,脚磕破了,你在草丛中找出它,它会为你疗伤。等你长大些,方方正正的汉字越认越多,你就能流畅地读唱那些草药汤头歌了:麻杏甘草石膏汤,四药组合有专长;肺热壅盛气喘急,辛凉疏泄此法良。大黄附子细辛汤,胁下寒凝疝痛方;冷积内结成实证,温下寒实可复康……它们充满韵律,更充满智慧和怜悯。再长大些,你一定要读一读辛弃疾的《静夜思》:“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流黄。柏影桂枝相映,从容起、弄水银塘。连翘首,掠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菊老伴花黄。”百草的世界,是百药,是诗词,也是人生,还是仁心仁德、无为而治、万物渐进、天人合一……
的春天,我想找一根草叶写下爱和感恩,让它在我松开手的刹那弹起时,将这爱和感恩带给广阔天地、自然诸神。也传给你,亲爱的孩子!
全文完
夜晚(一)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曾拥有夜晚,尽管我们随着落日走进它里面,却也不能拥有它。我们结伴滞留在它的华灯下狂歌或者制造其他的喧嚣,企图用声音占满它;我们坐在电视机前,将遥控器摁来摁去,纠缠于一堆无聊的剧情——当然也会碰上真正的艺术品——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直至夜愈来愈深。就算如此,还是不能拥有它,反而是它用一张时间的黑网将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地网去,毫不费力。或许,你会反驳,既然做这些都不能拥有它,那睡眠该是吧!夜晚的确是适合睡眠的,它黑下来,就是想让世间万物安静地歇息一回,白天够闹够累了,必须有一个暗夜来安抚、平衡一下。可是,我们在它身体里的大多数睡眠也只是服从于它的安排,跟拥有它还有着本质的区别。小时候,在无数个春日的清晨跑到菜地、瓜墩前,总能发现奇迹——或是成千上万的白菜籽发了芽,或是一粒豌豆、一颗南瓜子破土而出。夏日,用叶子轻轻盖住一些小芽,过了一晚,揭开叶子,发现那些白嫩的小芽变绿了,长高了一截,有的甚至不用揭,自己顶开了遮盖的树叶。为什么那些籽粒总是在夜晚生出来,总是在夜晚长高呢?白天,特意在瓜墩前一站老半天,怎么就不见它们钻出来,或者长高一点呢?或许是夜晚太神秘了,而生命也是一件神秘的事件,它们就那样契合了,于是,彼此拥有!我不知道。但我看见过,在夜晚,孩子安睡在摇篮里,安睡在母亲的怀抱,突然全身一激灵,这时母亲笑了:宝贝,又长了,又长了一寸。这夜晚的笑容,夜晚生命的激灵是多么生动啊!有一夜,我们将车开出老远,远到一个城市西北角偏僻的乡村。不经意间,车子开进一个岔道,我们迷路了。天空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车灯前的路很窄,车子无法调头,司机只好继续往前开。我坐在车后座,心中兀然暗自兴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向黑夜进发,深入了黑夜之中。那就往前走吧,看看它究竟通向哪里……但车子走了没多远就停下来了,抵达了一个村子。司机是一个谨慎的人,坐在我身旁的丈夫也是,他们几乎同时下了车,去看路况。我也钻出车门,眼睛暗适应后,我看见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户人家门前,一块长条石抵在路边,护住铺了水泥的的门前空地。夜很黑,很静,一黑到底,一静到底。我在那块石头上坐下来,因为心里头对这样的黑静无比认同,平常有些麻木的感觉骤然变得敏锐起来。我听见了整个村庄睡眠的鼻息,沉静、安逸,那样符合造物主的意愿。我听见无数黑黝黝的树在轻摇,还有——该是幽深锋利的剑杆芒在不远处随风而歌,它们的声音是独特的,无法模仿(事实上,世间万事万物的声音都是各各唯一的)。我永远记得它们的声音,那是一种疼痛而又快乐的声音——它们一定在那里。它们其实是容易让人流血的事物,需要小心触碰,愈老愈要小心避开。我还闻见了稻子的香味,黑暗处田野里的稻子一定是在灌浆,一鼻泛甜的香,久久不散……后来,我们就在那户人家的门前移开长条石,调转车头回到了熟路上。毕竟,夜太幽深了,而人终究胆小,不敢贸然闯“关”。我没能找见夜晚通向了哪里,但我敢肯定自己拥有了那个夜晚。它遍野的虫鸣,它的稻香,它的安睡和幽暗中歌唱不歇的剑杆芒,都是那样栩栩如生。有歌唱道: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是真的,我在一个远行的夜晚体察了这一点。那是一次真正的远离,几千里之外,向西,向敦煌,一个人的旅行。抵达目的地,洗过澡,在宾馆洗得发白的床单上躺下来,我以为我会马上入睡——我都两天三夜端坐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没有睡一个囫囵觉了呀,双腿肿得难看。可奇怪的是,尽管头很沉,竟然睡不着,把上帝的羊羔数了无数,脑子还是清醒得不得了。夜,不浅。我抵达宾馆的时间是晚十一点,梳洗一番,又数了半天羊,早该是午夜了吧。敦煌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午夜,很安静。灭掉房间里的灯,拉下双层的窗帘,在一片漆黑里,我闭着眼睛,顺其自然,停止数羊的挣扎,任凭该来的来,该见的见。我看见小面包车在夕阳下急速奔跑,那是西边黄昏九点的夕阳,红红的,圆圆的,挂在矮矮的天空,带着那绝色的温静光芒久久不落。车窗外,一坨坨骆驼刺不断闪过,它们很健康,开着细微的收敛的红花……事实确是这样,小面包车很旧,车窗玻璃早被路途的风沙磨得模模糊糊的,坐在里面赶路的时候,我虽然很努力地看,也没能清楚地看见哪怕一棵骆驼刺的样子。只是后来,车内有客下车休息,我挤下来,跑到路边,蹲下身去,才借着朦胧的夜色看见了在丰水的南方从没见过的骆驼刺。现在,在黑暗的房间,我反而将它们看得清清楚楚——它们身上每一枚尖锐的刺,它们的花,它们坚硬的生命痛楚的坚持和它们深深的根须下贫瘠而辽阔的戈壁滩……那种辽阔超出了我的想象,在那里,我被忽略不计,我不存在。白天不懂夜的黑。黑夜里,一些事物反而愈加清晰,就譬如这骆驼刺,这辽阔……在一望无际的辽阔里,有爱——天爱地,地爱骆驼刺,骆驼刺爱戈壁滩上空的明月。那天夜晚,也许是数了上帝的羊的缘故,我还看见了一幅画,是高更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高更的书《生命的热情何在——高更大溪地之旅》我买了有两年了。在那本书里,我首次看见那幅画。书页里的画幅很小,有些东西根本看不清楚。后来,无意中从网上又看到那幅画。我不断地点击鼠标,放大,放大,希望能看清画里的一切。但很遗憾,当放到最大,画面的颗粒越来越粗,画里的一切反而模糊了,总有部分画幅掩进屏幕深处,必须左右或上下移动,它们才能一点点显现出某一局部来。在闭着眼的夜晚,它却清晰起来——鸽子,初生的婴儿,摘果的亚当,青春正盛的女人和披一头灰发的老者……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那里去?夜晚,眼睛用视紫红质寻找。夜晚,我等着幸福入睡如婴儿。(二)我有一种偏执的感觉,觉得许许多多的人可以把白天过成同一个样子,但夜晚却会是各各不同的。这感觉既源自于我个人对夜晚的偏爱和敏感,也源自于我相信在夜晚,一切人和事都有不知不觉地回归本原的倾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找不出两枚一模一样的鸡蛋——在夜晚,不经意间回到自我的人们,梦会是一样的吗?在夜晚,不经意间回到了最本真状态的生命,脆弱的,因为夜晚的黑可能更脆弱;强悍的,在夜晚的黑里,也可能悄悄蛰伏或滋长一股新的力量。过去,有整整十年,医院紧密相连,一所在乡间,一所在城里。十年里的那些夜晚,那些上夜班的夜晚,一个人守在病区的夜晚是不同寻常的,有着复杂的特质和气味。一个人,穿着白大褂,守护着病区数十张床位,倾听、分辨占据这些床位的人们的鼻息,使用器具、药物、话语……等在职责范围内允许的方式方法安抚他们的鼻息,使之得以延续、趋于平稳或安享这最平常的一呼一吸的快乐,这是一份难得的好职业,对女性而言尤好——众目所见,在掠取和守护之间,女性更热衷于后者,女人生来就是喜好守护和善于守护的。一直心怀感恩,感恩这份职业和这份职业的夜晚成全了我,不仅使我身上与生俱来的母性得到充分释放,更为我忱于想象提供了时机和空间。在最初的一些夜晚,病房里很安静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象过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克里米亚大战,想象过那个名叫南丁格尔的英国女人在战地上实施救护时的劳碌和心态。一个美丽的女人充满热忱地闯入战地,把自己与炮火、血、烟尘和从头顶呼啸而过的流弹连在一起。男人在那里制造死亡,制造妻离子散,制造鲜血,而她却在那里缝合创伤,嫁接残损后的期冀。因为这样一个女人,英国士兵的死亡率由40%下降至2.2%;因为这样一个女人,鲜血也变得含情脉脉……这样想着的时候,觉得自己身处的夜晚,辛勤守护的夜晚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职业的光荣和梦想成了我平庸生命的光荣和梦想,被光荣和梦想激励的这些夜晚是琐屑的,也是母性的,充实的,它们没有虚度。后来,随着一个个夜晚的重临,不断有新的想象替代旧的想象。你看,病区的走廊老长老长的,一个人从这头走到那头,总能想些什么。譬如有一夜,走到走廊的尽头,推开最后那扇虚掩的房门,看见那个陪坐在丈夫病床一侧面色戚戚的女人,我忍不住想:他们会怎么发展下去呢?胃囊的破口可用丝线缝合,而爱情的裂缝缝得拢,抚得平吗?他们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人出轨,女人用水果刀刺伤了他的肚腹。事实上,连通着走廊的每一扇木门里都有故事。哀唤、忍耐、忧心、焦灼短暂缓解的舒适……年老的、年轻的身体在这里,在深深的走廊的木门里,大体上是一种痛的伤的情态——各处的伤,各处的痛,各处的病,形形色色。“我们并不知道死亡是否可以让人如意/至少活着的生活不是如此”。当先知先觉的诗人在此叹一口气时,我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我说过,十年的那些夜晚有着复杂的特质和气味。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种特质复杂在哪里,但气味是确定无疑的,是生的气味、死的气味和生死较量的气味。刚入夜,患有严重哮喘的老者艰难地停止了呼吸。夜再深一点,因为中暑而昏迷的农妇苏醒过来。曙色初露时,一个新生儿大声啼哭着来到了人世。就是这样,奔生,奔死,充溢着浓厚的气味。病区的走廊为什么那么长,那么深呢?在乡间,昏黄的灯影将走廊拉得更长。有时,我走过去,软底的护士鞋仅仅发出微不足道的轻响。突然地,一阵风将走廊尽头的木门吹开了,凛凛暗夜闯进来,随之一道闯进来的似乎还有一些小猫小狗样含混不清的哭叫声,我感到头皮发紧……我相信那些声音真实存在,就存在于木门外的野地。听说那里是一些长成和没长成的赤裸裸的被称作新生命又因为各种复杂或简单的原因死去了的生命体的坟地。那里是荒芜的,生满杂草。在绿色的节季,白天的阳光下,我依凭木门外的栏杆远眺过那里:它的荒芜很茂盛,和四周的田野、山峦一样茂盛。只是一片野地,没有什么异常。但那个起风的夜晚真黑呀!黑暗中的那个方位充满了诡异。那些小猫小狗样含混不清的哭叫声破门而入,是因为黑,因为冷,因为饿,还是因为想要寻找娘亲的怀抱呢?难道把它们一个个安顿到那里的汪家娘没把它们包裹好吗?汪家娘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妇,医院的清洁工。印象中,她没有过多的言语,总在安静地打扫。那片僻静的坟地是她选择的吗?她怎样掩埋下第一个不幸的生命幼体?我猜测她的掩埋工作一定是在长长的夜晚进行的。要么是等到入夜后,要么是趁着天还未亮之前进行。我从没看过她掩埋,也没有问过。她是个不言不语的老妇,满头银灰,慈眉善目,总是在病房里安静地打扫,或在产房里安静地清洗血污。从她身边走过,我偶尔慌张的脚步会不自觉地慢下来,仿佛被她身上的那份安静穿透。真是遗憾哪,说什么也应该随她一起去掩埋一次的,哪怕仅仅为着一个仪式,也该去一次。那些赤条条的生命,那些未长成的孩子,汪家娘先会清洗,然后该是用洁净的布单包裹,轻轻放入温软的泥土中,像种下一粒种子,再然后会为它们垒起小土堆吧。她掩埋的时候祈祷吗?这,只有夜晚听得见,只有那些茂盛地生长的杂草听得见,只有那片荒芜听得见,还有那些在夏夜亮着灯盏飞过野地的萤火虫,它们也会听见的。从病区这个视角看过去,夜晚从来都不是真正寂静的。夜晚的生命世象纷繁杂沓。在夜将尽未尽的时刻,守候了很久的那个人停止了呼吸。房间空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他还睡在那里。我们素昧平生却相处了很久。首先是他在昏睡中坚持了很久。他既脆弱又坚韧,为了能够呼吸,不惜忍受我们切开他的器官,插入一个银质的导管。借着这根导管,他向我,向所有来看他的人展现他的生命力。许多个夜晚,他的亲人轮流守候,握着他的手。母亲喜欢摸他的头,唤他,埋怨他,一边埋怨地唤一边流泪。而这一夜将尽未尽,他走了,母亲还守在那里,她糊涂了,一定以为儿子还睡在床上——一个人的消失是需要时间来确认的,至亲的人甚至需要用一辈子来忘记。十年间,最难忘的是在乡下病区的那一夜:女人为不能动弹的丈夫擦洗过后,将收音机拧开,放在他的耳边。几个月了,人们都说她的丈夫成了植物人,她不言语,坚持让丈夫听收音机。那一夜,奇迹发生了,收音机里唱的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一颗眼泪从那个人深陷的眼窝里流出来……灯火辉煌是夜晚。星光点点是夜晚。漆黑一团是夜晚。那个单薄的女人苦苦守候,终于等来了一颗泪珠——这颗咸涩的生命之水,足可载我们抵达翘首遥望的彼岸!全文完
作者简介▲▲▲艾芸艾芸,本名彭爱云,湖北大冶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月末,做过护士、记者、副刊编纂、妇联干部,现供职于大冶市政协。专业写作,著有散文集《期待一粒雪的冬季》。
《黄石文学》第期
责任编辑/薛俊杰
黄石文学喜欢本文作者,给个赞!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yuxingcaoa.com/yxcfz/8967.html


